鞭笞
鞭笞(拉丁语 flagellum,意为“鞭子”),又称鞭打或抽打,是指用特制的工具(例如鞭子、棍棒、树枝、九尾猫鞭、长鞭、鞭绳等)击打人体的行为。通常情况下,鞭笞作为一种惩罚手段被施加在不情愿的对象身上;然而,在某些情况下,鞭笞也可以是自愿接受的,甚至由个人在虐恋或宗教背景下自行实施。
鞭打的目标通常是裸露的背部,但也可以针对身体的其他部位进行。在某种程度上有所节制的鞭笞形式被称为“笞刑”(bastinado),此时裸露的脚底成为击打的目标(参见脚底鞭刑)。
在某些情况下,“鞭打”一词被宽泛地用于指代任何形式的体罚,包括用荆条鞭打(birching)或用藤杖抽打(caning)。然而,在英国法律术语中,曾经区分(目前在某些前殖民地领地仍然如此)“鞭笞”(用九尾猫鞭进行)和“鞭打”(以前用鞭子进行,但自19世纪初起改用荆条)。在英国,这两种形式的体罚都于1948年废除。
作为惩罚的现状
尽管在大多数国家鞭笞或鞭打(包括某些国家的脚底鞭刑)已被正式废除,但在世界某些地区,尤其是在实行伊斯兰法的国家以及一些前英国殖民地,鞭笞仍然是一种常见的惩罚手段。藤条抽打(caning)仍被法院作为某些犯罪类别的惩罚常规判处,例如在新加坡、文莱、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坦桑尼亚、津巴布韦等地。
叙利亚
在叙利亚,针对政治异议人士、战俘以及平民的酷刑极为普遍,其中鞭笞已成为最常见的酷刑形式之一。鞭笞被叙利亚自由军和叙利亚阿拉伯军队广泛使用,但叙利亚民主力量并未采用这种手段。ISIS(“伊斯兰国”)则经常使用鞭笞作为惩罚形式,通常将人绑在天花板上进行鞭打。在拉卡体育场(Raqqa Stadium)这座被临时改建为监狱的场所中,鞭笞是极为常见的酷刑方式。
此外,违反ISIS严格法律的人也经常被公开鞭笞。
作为惩罚的历史使用
犹太教
根据《托拉》(Torah,申命记 25:1–3)和拉比法(Rabbinic law),鞭笞可以作为对未达到死刑标准的罪行的处罚,但不得超过40下。然而,在没有公会(Sanhedrin)的情况下,犹太法并不实施体罚。根据《哈拉卡》(Halakha),鞭笞必须以三下为一组进行,因此总数不得超过39下。此外,在鞭打之前,需先判断受刑人是否能够承受惩罚,如果不能,鞭打数目会减少。犹太律法将鞭笞限制在40下以内,而实际执行时通常为39下,以避免因计数错误而违反律法的可能性。
古代
在罗马帝国,鞭笞通常被用作钉十字架之前的刑罚前奏,在这种语境下,有时被称为刑鞭(scourging)。最著名的例子是,据福音书记载,在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之前曾遭受鞭笞。鞭笞的方式和程度可能因当地习俗而有所限制,但其执行依据的是罗马法律。
鞭子通常在末端嵌有金属或骨头的小块,这种工具可能会导致明显的毁容和严重创伤,例如撕裂身体组织或损失眼睛。除了造成剧烈疼痛外,受刑者因失血可能进入低血容量性休克(hypovolemic shock)的状态。
罗马人将这种惩罚保留给非公民,根据《波尔夏法》(lex Porcia)和《森普罗尼亚法》(lex Sempronia)的规定(分别制定于公元前195年和公元前123年)。诗人贺拉斯(Horace)在其《讽刺诗》(Satires)中提到“可怕的鞭笞”(horribile flagellum)。通常情况下,受刑者会被剥光衣服,并绑在低矮的柱子上以便弯下身子,或被锁链绑在直立的柱子上以拉伸身体。两名执法官(有报道称最多可达四名或六名)轮流从裸露的肩膀一直鞭打到脚底。鞭打次数没有限制,由执法官自行决定,但通常不应致死。然而,李维(Livy)、苏埃托尼乌斯(Suetonius)和约瑟夫斯(Josephus)均记载过受刑者在柱子上被活活鞭死的案例。一些作者将鞭笞称为“半死刑”,因为许多受刑者在刑罚后不久便死亡。西塞罗(Cicero)在《控维雷斯》(In Verrem)中写道:“pro mortuo sublatus brevi postea mortuus”(“被当成死者抬走,随后不久便死亡”)。
中世纪至近现代
1530年,英国通过了《鞭笞法案》(The Whipping Act)。根据该法案,流浪者会被带到附近的居民区,“在那里被绑在车尾赤身裸体地用鞭子抽打,穿过整个集市,直到身体流血”。
在英国,罪犯(主要是盗窃罪犯)通常被判“在车尾鞭打”,即沿着犯罪现场附近的街道公开鞭打,直到“他的[或她的]背部流血”。然而,从17世纪后期开始,法院偶尔会下令在监狱或教养院内进行鞭打,而不是在街头。从1720年代起,法院开始明确区分私人鞭打和公开鞭打。在18世纪至19世纪初,公开鞭打的比例逐渐减少,但私人鞭打的数量却有所增加。1817年,英国废除了对女性的公开鞭打(早在1770年代就已逐渐减少),而对男性的公开鞭打则在1830年代初停止,直到1862年才正式废除。
对男性在监狱内的私人鞭打持续至1948年才被废止。1948年的废除并未影响监狱巡回法官(visiting justices)对犯下严重攻击罪行的囚犯判处荆条或九尾猫鞭的权力(适用于英格兰和威尔士,但苏格兰除彼得黑德监狱外并不适用)。这种权力直到1967年才被废除,而最后一次使用是在1962年。公立学校的鞭打于1986年被禁止,而私立学校则在1998年至2003年期间逐步被禁止。
在法国大革命期间,鞭打虽非官方惩罚,但也曾发生。1793年5月31日,雅各宾派妇女绑架了革命领导人安妮·约瑟夫·泰罗尼·德·梅里库尔(Anne Josephe Theroigne de Mericourt),将她剥光衣服,在杜伊勒里宫的公共花园中当众鞭打其裸露的臀部。遭受此羞辱后,她拒绝再穿任何衣物,以此纪念她所受的耻辱。她最终精神失常,在疯人院中度过余生。
在俄罗斯帝国中,使用鞭子(knouts)对刑事犯和政治犯进行鞭打。通常情况下,判处100鞭的刑罚会导致受刑者死亡。鞭打也被用作对俄罗斯农奴的惩罚。
2016年,沙特阿拉伯诗人阿什拉夫·法亚德(Ashraf Fayadh)因“叛教”被判处8年监禁和800次鞭刑,而未被判死刑。2020年4月,沙特阿拉伯宣布将鞭笞替换为监禁或罚款。
对奴隶的使用
鞭笞曾被用作对奴隶的纪律惩罚。在美国奴隶制期间,奴隶主和奴隶经常遭受鞭打。奴隶巡逻队(slave patrolers)也被赋予权力鞭打任何违反奴隶法的奴隶。历史学家指出,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也批准过对奴隶的鞭打。
历史学家迈克尔·迪克曼(Michael Dickman)表示:“[奴隶主]用鞭子作为工具来强制执行他们对社会的构想。而奴隶通过他们所受的惩罚和压迫,将鞭子视为奴隶制度压迫的具体象征。”1863年,一张名为“被鞭打的彼得”(Whipped Peter)的照片流传甚广。照片中,一名奴隶的背部布满了因鞭打而留下的伤痕。这张照片激起了人们对奴隶制暴行的愤怒,并在南北战争期间助推了反奴隶制情绪。
作为军事惩罚的鞭笞
在18至19世纪,欧洲军队对普通士兵实施鞭笞,作为违反军规的惩罚手段。
美国
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美国国会将士兵因军事法庭判决被鞭笞的法定上限从39下提高到了100下。
在1815年之前,美国海军舰长在纪律问题上拥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现存的航海日志显示,大多数情况下,舰长会根据罪行的严重性判处12到24下鞭笞。然而,也有个别情况,例如舰长艾萨克·昌西(Isaac Chauncey),判处了一百次或更多的鞭笞。
1815年,美国海军规定舰长能够判处的鞭笞上限为12下,超出此限的严重违法行为需要通过军事法庭审理。随着对海军舰船上鞭笞行为的批评声越来越多,美国海军部于1846年开始要求每艘军舰的舰长提交年度纪律报告,其中包括鞭笞的使用情况,并将鞭笞的次数限制在最多12下。这些年度报告由每艘舰船的舰长汇总后提交给海军部长,以便部长向美国国会报告鞭笞的普遍程度以及具体使用情况。
据统计,仅在1846年至1847年之间,在60艘海军舰船上共报告实施了5,036次鞭笞。最终,在新罕布什尔州参议员约翰·P·黑尔(John P. Hale)的推动下,美国国会于1850年9月通过了一项当时颇具争议的法案修正案,禁止在所有美国舰船上使用鞭笞。这一修正案被纳入了一项海军拨款法案中。
黑尔的倡议受到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在其半自传体小说《白夹克》(White Jacket)中对鞭笞的生动描述的启发。梅尔维尔将鞭笞描绘为19世纪海军纪律中一种残酷的常规惩罚。1843年至1844年间,梅尔维尔服役于美国护卫舰“美国号”(USS United States),根据该舰的航海日志记载,在此期间发生了163次鞭笞,其中包括梅尔维尔于1843年8月18日和19日刚抵达夏威夷火奴鲁鲁(Honolulu, Oahu)时便目睹的鞭笞。
梅尔维尔在其更著名的作品《白鲸》(Moby-Dick)中,也对鞭笞及其相关情境进行了强烈而深刻的描写。
英国
在英国,鞭笞作为一种惩罚形式极为常见,以至于藤条抽打(caning)、打屁股(spanking)和鞭打(whipping)被称为“英国恶习”(the English vice)。
皇家海军中的鞭笞
鞭笞是英国皇家海军中一种常见的纪律措施,与水手们对疼痛的男子气概般的漠视联系在一起。一般来说,军官不会被鞭笞。然而,1745年,如果一名被革职的英国军官受到侮辱,其佩剑可能会被当众折断,甚至遭受其他形式的羞辱。
在军舰上,“九尾猫鞭”(cat o’ nine tails)常用于严厉的正式处罚,而“绳尾”(rope’s end)或“起子”(starter)则用于非正式的即时惩罚。在1790年至1820年期间,皇家海军平均每次鞭笞为19.5下。一些舰长,例如托马斯·马斯特曼·哈迪(Thomas Masterman Hardy),施加了更为严厉的惩罚。哈迪在1803年至1805年指挥“胜利号”(HMS Victory)时,将处罚标准从原来的十二下和二十四下(针对较严重的罪行)提升到三十六下,并对如盗窃或累犯等更严重的罪行判处六十下。
在极端情况下,犯人可能会被“全舰队鞭笞”(flogged around the fleet):将大量的鞭笞(最多600下)分配到舰队中的各艘船只上,犯人被带到每艘船上受刑。如果是在港口,则犯人会被绑在船的小艇上,划过舰队,所有舰船的船员被召集观看惩罚。
鞭笞的废除
1879年6月,英国下议院就废除皇家海军中的鞭笞展开辩论。梅奥郡议员约翰·奥康纳·鲍尔(John O’Connor Power)要求第一海军大臣将“九尾猫鞭”带到议会图书馆,以便议员们能够亲眼看到他们正在辩论的对象。这场辩论被称为“九尾猫事件”(the Great ‘Cat’ Contention)。鲍尔在议会中说:“既然政府已经将‘猫’放出袋子,那我们也只能勇敢面对了。”诗人桂冠泰德·休斯(Ted Hughes)在其诗作《威尔弗雷德·欧文的照片》(Wilfred Owen’s Photographs)中提及了这一事件:“一位机智又深刻的爱尔兰人要求将‘猫’带入议会,并坐在那里观察绅士们把玩它染血的鞭梢。结果……悄然无声地,议案通过了。”
拿破仑战争期间的鞭笞
在拿破仑战争期间,英国陆军对士兵施加的鞭笞上限达到1,200下,这样的刑罚足以永久致残或致死。半岛战争历史学家查尔斯·奥曼(Charles Oman)提到,在整个六年战争中,这样的最高刑罚通过军事法庭仅执行了九到十次,而有约50次执行了1,000下鞭笞。其他刑罚包括900下、700下、500下和300下。一次,有士兵因偷窃蜂巢而被判700下鞭笞。另有一名士兵在被判400下鞭笞后仅执行了175下便被释放,但随后在医院中住了三周。
在战争后期,更严厉的惩罚被废除,犯人被流放至新南威尔士,而在那里的殖民地中往往还会遭受更多鞭笞(参见澳大利亚惩教殖民地部分)。奥曼后来写道:
“如果有什么能让一支军队变得残暴,那就是英国军事惩罚法规中这种邪恶的残酷,而威灵顿公爵终其一生都支持这种法规。许多权威记载表明,一个士兵因一个微不足道的过错,或因并不涉及道德罪责的过错而被鞭笞500下,往往会从一名好士兵变成一名坏士兵,因为他失去了自尊,并对正义的感知彻底麻木。优秀的军官对此心知肚明,并尽力避免使用九尾猫鞭,而是尝试更理性的手段——而且多数情况下非常成功。”
英国皇家安格利亚团第三营(3rd Battalion’s Royal Anglian Regiment)的绰号“钢背”(The Steelbacks)来源于其前身之一,第48(北安普敦郡)步兵团(48th Northamptonshire Regiment of Foot)。该绰号反映了他们在面对九尾猫鞭鞭笞时的坚韧表现(“在鞭笞下没有一声呻吟”),这一惩罚方式在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的英国陆军中司空见惯。
北爱尔兰特别权力法案
北爱尔兰建立后不久,1922年北爱尔兰议会通过了《特别权力法案》(Special Powers Act),也被称为“鞭笞法案”(Flogging Act)。该法案授权政府“采取一切必要步骤并发布一切必要命令,以维护和平与秩序”。长期担任内政部长的道森·贝茨(Dawson Bates,1921–1943)被授予权力,可为维护法律与秩序制定任何必要规定。违反这些规定可能被判处最多一年监禁和强制劳动,而某些罪行则可被判鞭笞。
该法案一直有效至1973年,随后被《北爱尔兰紧急条款法案》(Northern Ireland Emergency Provisions Act 1973)取代。一名曾于1942年被鞭笞的爱尔兰共和军囚犯弗兰克·莫里斯(Frank Morris)回忆他的15下“九尾猫鞭”:“那种疼痛难以想象;尾端的鞭绳将我的肉切到骨头,但我决心不喊叫,我也没有。”
其他相关事例
英国王家德国军团(King’s German Legion,KGL)是受英国资助的德国部队,他们不执行鞭笞。曾有一名驻扎在军团中的英国士兵被判鞭笞,但德国指挥官拒绝执行。在1814年英国第73步兵团(73rd Foot)在法国占领区对一名士兵实施鞭笞后,愤怒的法国市民对此提出抗议。
法国
在法国革命战争期间,法国军队完全废除了鞭笞,转而施行死刑或其他严重的体罚。
澳大利亚惩教殖民地
鞭笞曾是英国陆军和皇家海军的常见纪律手段,也在早期澳大利亚殖民地的惩教系统中占据显著位置。由于流放到澳大利亚的罪犯已经“被监禁”,因此他们在殖民地中的犯罪通常不会被判监禁,而是以体罚形式惩罚,例如强制劳动或鞭笞。
鞭笞通常使用单鞭或更臭名昭著的九尾猫鞭进行。犯人上身通常被剥光,并被悬挂在由三根木梁组成的三脚架下(称为“三角架”)。许多情况下,犯人的双脚几乎触不到地面,这有助于将皮肤拉得更紧,从而增加鞭笞的伤害。此外,这种姿势将犯人的重量集中于肩部,进一步加重了痛苦。
在受刑过程中,一名或两名执行者会按照规定的次数鞭打犯人的背部。在鞭笞期间,会定期咨询医生或其他医务人员,以了解犯人的状况。然而,医务人员通常只是观察犯人是否仍然清醒。如果犯人昏迷,医生会暂停刑罚,直到犯人被唤醒,然后继续鞭打。
女性犯人也会被鞭笞,无论是在罪犯船上还是殖民地中。尽管她们通常被判较男性更少的鞭笞(通常每次限制在40下以内),但鞭笞的方式与男性并无不同。
鞭笞通常是公开进行的,全体殖民地成员会被召集观看。这不仅是对犯人的身体惩罚,也是一种羞辱,并通过强制展示服从权威的姿态来警告其他人。
鞭笞结束后,犯人被鞭打得皮开肉绽的背部通常会用盐水冲洗,作为一种粗糙而痛苦的消毒手段。
即便在澳大利亚独立后,鞭笞仍持续了多年。最后一次鞭笞发生在1958年,威廉·约翰·奥米利(William John O’Meally)在墨尔本彭特里奇监狱(Pentridge Prison)被执行了鞭刑。
作为宗教实践
古代
在古罗马的Lupercalia节庆期间,年轻男子手持用刚刚献祭的山羊皮制成的皮鞭,奔跑在街道上,用这些皮鞭抽打他人。据普鲁塔克记载,妇女会主动伸出手接受鞭打,因为她们相信这可以帮助她们怀孕或让分娩更加顺利。
祭祀女神西贝勒(Cybele)的阉人祭司(galli)在名为“血之日”(Dies Sanguinis)的年度节日中会鞭打自己,直到流血。此外,希腊-罗马的神秘宗教(mystery religions)的入会仪式有时也包括仪式性的鞭笞,斯巴达崇拜阿尔忒弥斯·奥尔西亚(Artemis Orthia)的仪式亦然。
基督教
在基督教语境中,“鞭笞”通常指耶稣受难过程中、被钉十字架之前遭受的鞭打。出于宗教目的的“肉体的克制”(mortification of the flesh)自1054年的东西教会大分裂以来,被各种基督教派别的成员所采用。如今,这种作为忏悔工具的器具被称为“惩戒鞭”(discipline),通常是一种由打结的绳索制成的鞭子,用于在私人祈祷中反复抽打肩膀。
在13世纪,一群被称为“鞭笞者”(Flagellants)的罗马天主教徒将自我克制的行为推向极端。他们会走街串巷,公开鞭打自己和彼此,同时宣讲忏悔。这些场面因其本质上颇为病态和无序,曾在某些时期被当局取缔。然而,这种行为在之后数个世纪内反复出现,直至16世纪。
在黑死病流行期间,鞭笞作为一种净化罪孽、避免感染疾病的手段也被广泛实践。1348年,教皇克莱孟六世(Pope Clement VI)曾允许这种行为,但次年又将鞭笞者定性为异端,并予以谴责。
新教改革者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在脱离罗马天主教之前,曾定期进行自我鞭笞,以作为肉体克制的一种方式。同样,公理会作家萨拉·奥斯本(Sarah Osborn,1714–1796)也曾通过自我鞭笞来提醒自己在上帝眼中的持续罪恶、堕落和卑微。
在19世纪30年代开始的牛津运动(Oxford Movement)中,隶属英国圣公会的许多成员也普遍采用惩戒鞭进行自我鞭笞。例如,19世纪末的法国圣衣会女修道士圣德兰(St. Thérèse of Lisieux),被天主教会认为是教会圣师(Doctor of the Church),是一个具有影响力的例子。她对身体忏悔的态度质疑了传统的观点,认为每天生活中痛苦的爱心接纳比额外的身体惩罚更能取悦上帝,并能更好地促进人与人之间的爱。尽管如此,作为圣衣会的一员,圣德兰仍然实践了自愿的身体克制。
一些严格修道会的成员,以及天主教平信徒组织主业会(Opus Dei)的部分成员,仍然使用惩戒鞭进行轻度的自我鞭笞。据报道,教皇圣若望·保禄二世(Pope John Paul II)也曾定期使用惩戒鞭。目前,自我鞭笞在哥伦比亚、菲律宾、墨西哥、西班牙以及秘鲁的一些修道院中仍然很常见。
什叶派伊斯兰教
在什叶派伊斯兰教中,用刀或链条切割身体(matam)的行为已被包括伊朗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Ali Khamenei)在内的什叶派马尔贾(marjas)明令禁止。作为替代,一些什叶派穆斯林以献血(称为“Qame Zani”)和鞭打(flailing)的方式表达哀悼。然而,仍有一些什叶派男性和男孩用链条(zanjeer)或长剑(talwar)自我鞭打,让鲜血自由流淌。
一些传统的鞭笞仪式包括使用长剑的“Talwar zani”(亦称“talwar ka matam”或“tatbir”),以及使用带有刀刃的链条进行的“zanjeer zani”或“zanjeer matam”。这些宗教仪式旨在表达对伊玛目侯赛因(Husayn)及其家人的团结情感。参与者为自己未能出现在卡尔巴拉战役中保护侯赛因及其家人感到悲痛。
在一些西方城市,什叶派社区会组织与红十字会等机构的献血活动,作为“塔特比尔”(Tatbir)和“Qame Zani”等自我鞭笞仪式的积极替代方式。
作为性实践
在BDSM(Bondage, Discipline, Dominance, Submission, Sadism, Masochism)的语境中,鞭笞(flagellation)也被用作一种性实践。与作为惩罚的鞭笞相比,其强度通常要低得多。
历史记录
关于人们自愿被绑缚或鞭打作为性爱前奏或替代的轶事,可以追溯到14世纪。至少从16世纪90年代开始,就有在情色背景下进行鞭笞的记录。例如,约翰·戴维斯(John Davies)的讽刺诗集中包含相关内容。
在17世纪的英国,鞭笞作为一种性实践更加广泛地被提及。例如,托马斯·沙德韦尔(Thomas Shadwell)的戏剧《博学者》(The Virtuoso, 1676)和蒂姆·特尔特罗思(Tim Tell-Troth)的《占星术的骗局》(Knavery of Astrology, 1680)都提到了所谓的“鞭笞学校”(flogging schools)。这些“学校”被认为是提供鞭笞服务的场所。
此外,17世纪晚期的艺术作品也为此提供了视觉证据。例如,大英博物馆收藏的一幅英国铜版画《受辱的情夫》(The Cully Flaug’d)描绘了与鞭笞相关的场景。
文学与出版物
约翰·克利兰(John Cleland)的小说《芳妮·希尔》(Fanny Hill,1749年出版)包含了一段主人公芳妮·希尔与巴维尔先生(Mr. Barville)之间的鞭笞情节。这一描写引发了人们对鞭笞作为情色实践的兴趣。
随后,大量与鞭笞相关的出版物涌现。例如,《时尚讲座:用荆条纪律编写并发表》(Fashionable Lectures: Composed and Delivered with Birch Discipline, 大约1761年)成为一部知名作品。该书不仅宣传了以鞭笞为主题的“讲座”,还列出了提供这种服务的女士名单,并描述了她们使用荆条或九尾猫鞭实施鞭笞的细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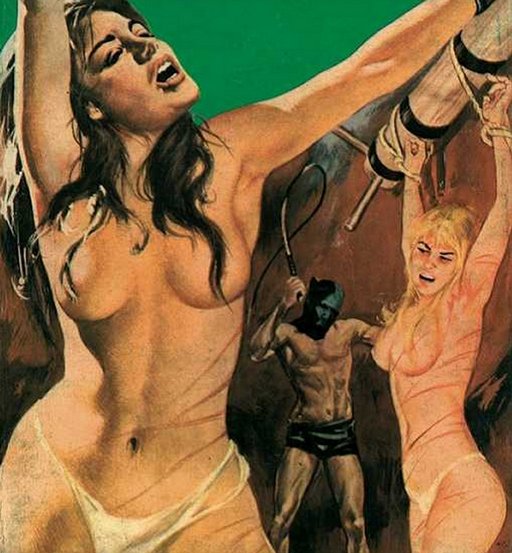



![[Art Video] 1874 職業Mの女 責め緊縛調教](https://bdsmwild.com/wp-content/uploads/2024/03/01545-art1874-bdsmwild-【Exclusive】Art-Video1874-職業Mの女-責め緊縛調教.webp)
.jpeg)

![[Tokyo bondage] TOKYO BONDAGE DAMSELS NN10-11 Beautiful Japanese Maid Nana Bound and Drooling Nana Akasaka [東京緊縛]](https://bdsmwild.com/wp-content/uploads/2023/06/00545-nn10-11-bdsmwild.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