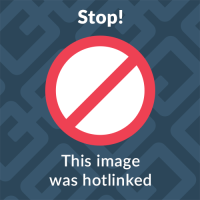那张弓是用铁桦木制成,沉甸甸的压手。为了保持弹性,牛筋制成的弓弦平时都是松的,弓身以一个自然的姿态张开,弓脊上刻着他的名字,韩丹。
他在黑暗中拧紧弓弦,然后左手握弓,右手套着指环的拇指扳住弓弦。将近十石的强弓在他手中缓缓拉开,瞄向天际的半轮新月。
脸上似乎还有篝火的灼热,强烈的心跳顺着手指传到弓弦上,似乎震得弓弦嗡嗡作响。韩丹把铁桦弓弯成满月,然后松开手指。那张空弓猛然弹起,弓弦“崩”发出一声震响。
韩丹出身于帝都军户,家中累世从军,到他已经是第五代了。他父亲戍守北疆时,由于误报了两颗首级,被以冒领军功论罪,病死狱中,家道沦落。十五岁时,韩丹带上这张弓,独自来到西陲,成为一名募卒。
去年帝宫内使赵衡来到西陲,校尉汲大人邀请诸国在金微山射猎,他作为卫兵随行。围猎中,有一头野猪穿过罗网,冲撞了一位贵宾的车驾,韩丹当即挽弓射杀野猪。事后他才知道,车内坐的是居桓王后。
韩丹从未见过这样高贵优雅的女人。在居桓王宫,宛王后接见了这个默默无闻的士卒,他清楚记得,当说自己来自帝都,宛王后那双眸子顿时明亮起来。那天宛王后问了很多,临别时又给了他一份丰厚的赏赐。这件事惊动了校尉大人,不久韩丹被调入都护府,成为汲大人的一名亲兵。
但现在,这张曾经救过居桓王后的弓,却要对准王后。
“你曾经见过王后,知道王后相貌。”汲大人对他说:“带上你的弓,如果不能赎回王后,就射杀她。”
韩丹一惊,“为什么?”
“因为王后是前来和亲的天朝王族,就是死也不能落在蛮族手里。”
军汉们的轰笑声不时传来,韩丹再次拉开弓,对着天际的明月射去。
*** *** *** ***
居桓残破的大门倒在地上,城墙上洒满发黑的血迹,还有火烧的烟痕。曾经有过四万居民的城市此时仿佛一座鬼域,远远就能闻到令人作呕的恶臭。
都护府的骑兵面色凝重,他们都是久经沙场的战士,单从痕迹就能判断出战斗的酷烈。不管敌人是谁,都绝不好惹。他们没有进城,因为这座充满尸臭的城市不可能再有人生存。
绕过城角,便看到草原上星落棋布的营帐。轲横的浓眉皱了起来。那些帐篷从城外一直绵延到蒲昌海,营内放牧的不仅有马,还有牛羊和猎犬,帐外除了粗野的男人,还有妇女和孩子。轲横嗅到一股不祥的气息。
以往草原的牧族袭击城邑,都是一击即退,来去如风,以免被九国大军合围。但这支敌军不仅仍然停留在居桓城外,而且还携带有老人和孩童,像是举族迁移到了居桓。
“轲将军!”冯竞扬起马鞭。
在部落营帐前方,树着一排高大的木干,上面一串串挂得尽是割下的头颅。木干后是一个巨大的火堆,焚烧尸体的臭气在远处就能闻到。轲横眼角跳了几下。自从天朝大军击溃魁朔以来,整个草原都未出现过如此嗜血的部族。至少轲横的军族生涯中从未见过。这是一支完全陌生的敌人。
营帐一阵骚动,刚才还在悠闲休憩的男人们,一瞬间就翻上马背,呼啸着朝这支车队驰来。
轲横摘下头盔,擎出代表使者的节杖,高举过顶,高声道:“西陲都护府使者轲横,要求见你们的主人!”
那些剃发的战士将他们围在中间,警觉地看着他们。过了一会儿,一个年轻的汉子跃马上前,“西陲都护府是什么地方?你们为什么要来这里?”
“你们是草原的主人,都护府是西陲的主人。”轲横缓缓说道:“从蒲昌海到狼硅山,九个王国都受都护府管辖。我是轲横,都护府的使者,想见到你们的主人。”
“我是拔海。”那个年轻人说道:“带领我们的是左部翎侯铁什干的儿子,英雄的铁由。”
不可伤害使者,是草原通行的法律。拔海朝族人呼喊几句,要人群为这支使者队伍分开一条道路。
*** *** *** ***
戴着黑铁头盔的首领坐在营帐中央,为了避免误解,轲横没有采取天朝流行的跪坐姿势,而是盘膝坐在首领面前,以显示出与对方至少相等的地位。
但这些野蛮人并没有在意这些细节,他们甚至没有要求轲横取下武器。
“你找我有什么事?”那个首领在问。
轲横重复了一遍都护府的职权,然后说道:“居桓是受都护府管辖的王国之一。校尉大人想知道,你们为什么要攻灭他管辖的王国,把无辜的人民变为奴隶。有什么事不可以用谈判解决,而要流血呢?”
首领旁边一个瘦长脸的汉子说道:“居桓的国王窃取了乌德勒汗的土地,我们只是取回自己应得的东西。”
“金微山是大地的屏障,山北的草原你们尽可以驰骋,但山南的土地受到西陲都护府的庇护。”
“所有生长青草的地方都是乌德勒汗的牧场!这片土地属于青穹和苍狼的子孙。”
这些草原上的穷鬼都他妈的是野蛮人!在他们猪狗一般的脑袋里,只要能够抢到的,都是上天赐予他们的礼物。轲横心里骂着,尽可能压住怒火说道:“校尉大人对他的子民非常关心,他想知道,居桓的人民和他们的国王是否安全?”
“你知道,都护府的使者。”他们的首领用尖锐的声音说道,“战败者失去土地和财富,这是草原的规则。我们在每个居桓人身上打下印记,宣告他们成为奴隶。居桓的国王,会被送到乌德勒汗座前,由圣主决定他的命运。”
“居桓的王后呢?”轲横问道。其实无论是他还是都护府的校尉大人,对居桓王的死活都不在意。居桓的国王可以再立,子民可以再生,但王后作为天朝王族,是天朝荣耀的象征,绝对不可以受辱。
“那个无耻的妖婆么?”瘦长脸的汉子说着,发出一阵奚落的笑声。
轲横一阵光火,这些不知道礼貌的胡狗!他一字一句说道:“居桓王后是帝都来的公主,天朝高贵的王族。她与天朝的尊严一样,不允许有任何侵犯。所有敢冒犯天朝者,都将被诛灭。”
帐内的草原战士们都跳了起来,罕多尔拔出刀大声说道:“你是在威胁我们吗?腾格汗的爪牙!”
轲横注视着刀锋,两手按着膝盖,端坐不动。
“苍狼的子孙不会接受恐吓。”首领说道:“我可以告诉你的是:她已经成为奴隶。”
轲横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道:“那么让我们按草原的规则行事。”
轲横打开面前的锦盒,“这里有五百两黄金,我还带来了一千匹上等丝绸和二十匹骏马。这些物品足够换取五百名奴隶。我把它们都献给你,只赎回居桓的王后和公主。”
这笔财富足以令任何人心动,尤其是骏马和丝绸,对草原的牧族有着莫大的诱惑力。但那个首领铁盔下的目光却没有丝毫波动,他说道:“收起来吧,她不会被赎回。”
轲横变了脸色,“草原上有不能被赎的奴隶吗?”
首领冷冷说道:“即使你搬出山一样高的黄金,也赎不回腾格汗的女儿。她永远都是毡房里的奴隶。”
轲横费尽口舌,那些野蛮人却毫不松口。他无法理解,宛王后只是一个柔弱的女人,但可这些野蛮人宁愿放弃一大笔财富,也不愿把她交还给都护府。
轲横说得口干舌燥,也没能说服他们,只好退让一步。
“这些物品的十分之一交给你们,我只希望能见到王后和公主,为校尉大人传递她们平安的消息。”
“恐怕你要失望了。”罕多尔说道:“居桓的公主已经被送往左部翎侯雄鹰铁什干的营地。”
“那么王后呢?”
罕多尔摸了摸鼻子,轲横这时才发现他的耳朵被人割去,只留下两只耳孔。
“她在这里。”
“我希望能见到王后陛下。”
罕多尔看了铁由一眼,后者摇了摇头。
“不。你不被允许。”
轲横心里再一次升起不祥的预感。他很清楚宛王后的身份对这些野蛮人意味着什么。很可能居桓的王后已经被某个首领收为侍妾。甚至是没有名份的女奴。这是对天朝尊严极为严重的污辱。校尉大人会为之震怒的。
“她是居桓的王后,天朝的王族,”轲横缓缓说道:“拥有西陲最尊贵的身份。即使不允许赎回,王后也必须受到与她身份相应的礼遇。任何失礼的行为,都将被视为对天朝的冒犯。”
瘦长脸的汉子傲慢地说道:“我们处置奴隶的方式,不需要别人来指点。这个流着毒血的妖婆,已经被指定为毡房的奴隶——一个与她地位相应的新身份。如果你有耐心停留,十天后的宴会上,她将作为女奴,为客人献酒。”
拔海起身说道:“请到营帐里安歇吧。明天日出时,我们再来谈判。关于战争的谈判。”
*** *** *** ***
“怎么样?”
轲横一进帐篷,手下的士卒们围拢过来。
轲横骂了句粗话,拿起水囊狠狠喝了几口。
“赵虎!”轲横唤来一名手下,“你立即回去报讯,说我们已经在城外见到攻陷居桓的蛮族。告诉校尉大人:这是一支举族迁移的蛮族,包括老人和儿童在内,将近两万人。有三分之一是能够作战的男人。居桓王和公主,连同大部分被俘的居桓人,已经作为奴隶被押送回后方。”
“奴隶!”随行的士卒有人惊呼。
轲横狠狠瞪了他一眼,继续说道:“我们没有居桓王后的确切消息,有传言说王后已经在城破时自尽。这些蛮族来历不详,口音与草原人相似,可能由草原深处迁移而来。他们装备很差,虽然有铁制的武器,但数量很少。最重要的一点,他们有着强烈的敌意。我请求校尉大人做好战斗的准备——他们是都护府的敌人。如果可能,请校尉大人立即派军队渡过若羌水,进攻这支蛮族。”
赵虎立即牵马,单骑返回月支。
剩下十九个人一片静默,他们都听出轲横话中的杀意。这一战已经无法避免。
“将军,我们怎么办?”
“把马匹喂饱,所有人都穿上铠甲,带上兵器,随时等待我的命令。还有,备好火种!”
士卒们互相看了一眼,默契地分头行动。
“韩丹。”
轲横叫住那个年轻的射手。
“王后在一间毡房里。”
韩丹一震。
轲横低声说道:“今晚你一个人去,做得利落些,得手后我们立即杀出去。”
校尉的命令只有他们两人知道。宛王后的死将是一个永远不许揭开的秘密,在送往帝都的奏书上,居桓王后会是在城陷时自尽,以死亡保全了自己的名节和天朝的尊严。
*** *** *** ***
堆在地上的木柴燃烧着,不时发出辟辟啪啪的爆响,简陋而狭小的毡房内,弥漫着烟气和汗水体臭混杂的味道。木柴的火光很微弱,房内布满大片大片的阴影。
一具曼妙的肉体赤条条趴在草地上,白滑的肌肤沾满水迹,湿淋淋闪动着火光的影子。她手脚都带着铁镣,由木楔牢牢钉在地上。一根粗糙的铁链系在她颈中,另一端吊在毡房中间木柱上,迫使她扬起头。两只丰腻的乳球垂在身下,随着她散乱的呼吸微微起伏,乳头已经被捏得红肿。
那女人跪伏在地上,一块破烂的羊皮搭在她腰间,使她看上去就像一匹带鞍的马。那只光溜溜的雪臀裸露在外,比最优美的白色母马还要圆润饱满。光润的臀沟朝两边张开,臀间肥滑白腻的美肉一片红肿。
任何人掀开门帘,都会看到那只没有任何遮掩的美臀和她股间敞露的阴户。原本柔艳动人的阴户高高鼓起,充血的花瓣红肿地翻开,里面淌出一条长长的浊白黏液。在这里,没有人顾及她那怕最卑微的尊严,她就像一头被豢养在毡房里的牝畜。
她已经不记得有多少时日,也算不清有多少粗鲁的野蛮人享用过她的肉体。就像她旁边那个失去双手的女人一样,仿佛陷入一个无法醒来的噩梦里,失去了时间和空间的意识。
在昏迷了两天两夜之后,女傅醒转过来。看到尊贵的女主人沦落为蛮族的女奴,带着铁镣,撅着屁股,被野蛮的胡虏像娼妓一样肆意奸淫,她愣住了。
“王后!”女傅凄叫一声。
她艰难地转过眼睛。
“王后!”女傅再次发出凄厉的叫声,然后咬断了自己的舌头。
她眼前一红,爆出一片灼目的血花。女傅吐出咬断的舌头,鲜血喷涌而出,染红了她眼前的一切。
毡房里似乎有人叫嚷,她看到人影在动。他们扳开女傅的嘴巴,把絮毛大团大团塞到女傅口中。
她以为自己会再一次目睹死亡,看到自己的侍女作为一名宁死守护贞洁的烈女,令她羞愧无地的自尽。刹那间,宛若兰也升起同样的念头。用死亡来结束屈辱,也许是最好的选择。
但那些絮毛止住了流血。女傅没有死,她再一次活了下来,却失去了舌头。这些天,她时昏时醒,身体像一朵被切下的鲜花,渐渐枯萎。
07
韩丹用刀尖划开毛毡,朝里看去,然后悄悄退开。经过长途跋涉,这些帐篷布满了灰尘和泥迹,夜里看起来几乎一模一样,想在里面找到王后,就像想从蒲昌海中找出一根青色的芦苇一样困难。但轲横说,王后是在一座毡房里。
毡房一般是用木杆搭成方形的框架,然后在上面铺些毛皮,结构比牧民的帐篷更简陋,也更容易区分。营地的毡房并不多,而且大都散落在营地边缘,没有太多的警戒。
韩丹换了双薄底的靴子,等营地的篝火熄灭,围坐高歌的蛮族人散开,就悄无声息地开始寻找。他一手握着弓,一手拿着刀,腰间插着三枝羽箭。要杀死宛王后,一枝箭就够了。
老妇人格伦掀开门帘,进入毡房。长久的操劳,使她的腰过早佝偻,胸前垂着两条花白的辫子又干又短,就像她曾经见过的那些贫苦牧民。每年国王登基的庆典上,她都会让侍女从城楼上撒下大批大批的钱币,赏赐给这些无依无靠的老人。
“不知道羞耻的妖婆。”老妇人鄙夷地唾在她身上。
王后闭上眼,木然承受着她的唾骂,就像她承受那些男人野蛮地侵犯一样。
格伦提来一只木桶,她挽起衣袖,抓起王后腰上的破羊皮,在水中浸湿,然后擦洗着王后的身体。她擦洗得十分用力,像是面对一只不洁的秽器般,充满了厌恶和鄙薄。
“没有一个男人愿意在此里过夜,他们说,一到夜里你的幻相就会消失,现出令人作呕的妖魔相。”
格伦麻利地拔出木楔,扯开铁链。每到夜晚,王后都会被囚进木笼。传说中,腾格汗妖婆爪牙都会魔法,夜幕降临后,她们会变化成各种样子,去吸取婴儿的鲜血。
但这天格伦没有打开木笼,她把破羊皮扔给王后,“把你羞耻的地方洗干净!”
污浊的液体从股间淌出,滴在裸露的草根上。沾满凉水的羊皮按在腹下,她身体顿时一颤。
格伦气咻咻道:“从来没见过你这样无耻的女人,你就像一匹不知道贞洁的母马,谁都可以骑到你身上。女人最羞耻的地方,在你身上却像一块没人要的烂羊皮,谁都可以捡起来擦他的靴子。真让人恶心!”
老妇人格伦举起双手,摇了摇头,然后把沦为女奴的王后束缚在地上,离开营帐。
一只手落在王后肩上,沿着她身体的曲线摸到她丰满的雪臀。那只手并不像别的男人一样粗暴,而是充满了好奇,似乎惊讶于她肌肤的柔嫩和光滑。
“为何你和其他女人不同?腾格汗的女儿。”铁由问:“你的脚很小也很软,好像你从来没有走过路一样。难道你从来没有挤过马奶,剪过羊毛?”
王后摇了摇头。
铁由不悦地皱起眉头,“我记得你并不是哑巴。”
王后低咳一声,用嘶哑的声音说道:“我的女儿呢?”
“她是献给我父亲的礼物。那个地方,离这里有两个月的路程。”
王后低声哭泣起来。
韩丹屏住呼吸,剧烈的心跳奇迹般平缓下来。毡房昏暗的篝火中,他看到一具完全不属于这里的身体。即使她长发被随便挽起,身上没有任何能证实身份的衣物和饰品,就像一个最卑贱的女奴,被赤裸着缚在毡房内,韩丹依然一眼就认出她与众不同的身份。
毡房里只有一个戴着铁盔的矮小蛮族,正用他肮脏的手抚摸王后高贵的肉体。韩丹心头一阵剧痛,此时即使校尉大人没有下令,他也会做出同样的选择。
韩丹挽起弓,三枝长箭同时架在弦上。
就在弓弦弹开的同时,那个矮小的野蛮人突然抬起头,目光闪电般朝他射来。
王后哭得梨花带雨,甚至没有听到弓弦的震响。她只觉得身上突然一痛,铁由坚硬的手指从她臀间拔出,一把抓住了飞来的箭矢。
“叮”的一声,间不容发之际,铁由用手里的箭枝挑住了射向王后咽喉那枝长箭的锋镝。
近在身前的金铁声惊动了王后,她泪眼模糊地抬起脸,正看到一枝毒蛇般乌黑的长箭朝她心口射来。
一只略带稚气的手伸出,硬生生抓住箭枝。锋利的箭头刺破了王后的肌肤,在她胸前溅出一点殷红的血迹。
王后惊恐地张大眼睛,生死只在毫厘之间。
“是你的族人。他们要杀你。”
毡房外传来马匹的嘶叫,杀伐声大起。
宛后突然明白过来,身体一阵剧颤。
*** *** *** ***
韩丹蓦然转身,张弓一箭射出。后面一名骑手中箭堕马,随即被夜色吞没。轲横挥起长刀,替他劈开一支冷箭,大声道:“入林!”
虽然他们早有准备,但从蛮族的营地一路冲杀出来,也只剩下五骑。那些虏狗有着出奇的凶悍和韧性,虽然座骑不及他们,却始终紧追不舍。那些粗弓劣箭射出来一点也不比他们逊色,至少有十名弟兄是在追击中被敌军射落。
这片胡杨林救了他们的命。再神骏的马匹也不可能在夜晚的林间疾驰。一入林,轲横等人就跳下马,徒步奔行,以免座骑被绊倒受伤。
胡杨林阻住了敌军,从小就在马背上生活的他们根本无法徒步竞逐。听到追兵的声音渐渐远去,轲横松了口气。
“死了吗?”
韩丹犹豫了一下,点了点头。
轲横拍了拍了他的肩,什么都没有说。
只有韩丹知道,他的箭并没有射中王后。但那已经不重要了。
*** *** *** ***
铁由的手掌被箭锋划破,滴下鲜红的血。
与死亡擦肩而过,那种刻骨的恐惧使王后无法克制地战栗着。良久她轻颤着问道:“为什么?”
那个受伤的男孩冷冰冰说道:“你是我的奴隶。在草原上,奴隶是主人的财物。”
*** *** *** ***
就在轲横等人突围的同时,都护府的军令也传至丹华,命令丹华军作为先锋,立即北上,渡过若羌水,与来敌交战。
丹华是西陲最弱的一国,所有能够骑马弯弓的战士不过两千八百人,还不及居桓军的四成。居桓有坚城可守,也仅仅抵抗了三天,这不足三千的弱兵,正面对敌还不如送死。
但文末鲜红的都护府印刺痛了丹华王的眼睛。在西陲,没有人敢违抗都护府的军令,那怕是让他们去死。
丹华王拖延一日,拼凑出两千骑兵,交给奉命前来指挥的都护府将尉马勇。
即使马勇全力驱策,这支丹华军也整整用了六天才抵达居桓城附近。
“这群疲狗!”马勇忿然骂道。
马勇军阶比轲横高,是都护府一名骑尉,擅长刀马。皇赫王朝设置的西陲都护府节制九国,驻军却不到两千人。一般情况下,都是用都护府的名义调动诸国军队,由都护府的将领指挥作战。
对他指挥的这两千丹华军,马勇满腹牢骚。“老子带着都护府的弟兄,轻骑一日一夜奔行两百多里。这群疲狗三百里走了六天!日他姥姥的,还打个屁仗!”
都护府的主力迟迟未动,随行的只有马勇十余亲信。他们也对丹华这些未战先疲的弱兵看不顺眼,如果是都护府军,这会儿说不定已经该打完仗班师了。
“将军,前面就是居桓,探路的斥侯也廖回来了。要不要我们几个弟兄先去趟一阵,振作一下士气?”
都护府军中都是百战之余,悍不畏死。几名勇健的军士跃马搦战,在阵前斩将破敌,最能鼓舞士气。天色还早,丹华军已经停止前进,忙着埋锅做饭。看他们那副熊样,马勇真有心拣几个杀来祭旗。他重重喘了口气,点了点头。
一骑飞奔而至,远远就叫道:“将军!有敌!”
正停下歇息的丹华军顿时慌成一团,匆忙上马。那名派去探敌的斥侯疾驰过来,在他后方,隐隐传来铁蹄的轰鸣。
十几名亲信随从不等主将吩咐,立即跨马上前,呼喝着弹压阵脚。那斥侯滚鞍下马,高声道:“报将军!”
“说!”
“胡狗的大营就在居桓城外,离此二十里。属下刚一靠近,就被发觉。那些胡狗都上了马,全速追来!”
“多少!”
“追来的约有千余。帐篷未曾看清,数目不下两千。”
两千帐,如果都是骑兵至少有八千。这两千丹华军还不够一口吃的。好在斥侯立刻说道:“营里有老弱妇孺,好像是举族迁移。”
马勇松了口气,这样算来,能作战的男子顶多四五千人,还有一拼之力。在西陲的都护府军一向是以少胜多,曾经以五百人破敌五千。一比二的比例并不算高。只不过马勇忘了,他指挥的不是都护府军,而是丹华军。
那些模样古怪的骑手呈扇形杂乱地围过来。马勇提起大刀,一马当先冲到阵前掠阵,十几名亲信紧紧跟在他身后。
拔海抬起手,草原的勇士们勒住马匹,隔着三十丈的距离,虎视眈眈地望着那一小队骑兵。
马勇高声道:“胡狗!敢与我相斗吗?”
一名都护府军士拉开弓,一箭射在拔海座骑蹄下,那座骑扬起前蹄,往后退了尺许。
拔海一扬下巴,“别矢里!”
一名穿着白羊皮袍的勇士从人群中驰出,他额前剃发,两侧却垂在身前。那些蛮族武士大多穿着肮脏的羊皮袍,黑乎乎又破又旧,只有他的皮袍却像新的一样,白得耀眼。
马勇和几名亲信心里同时闪过一个名字,射雕儿!
草原上射术最精湛的骑手能射下天上的大雕,为了表示对他们的敬重,他们被称为“射雕儿”,以白衣为标志。这是一种古老风俗,没想到在这个野蛮部族中还保留着。
马勇长于刀马,射术还在其次。他的亲信丁承一磕马刺,策骑奔向一侧。
在族人的欢呼声中,别矢里纵马驰往另外一边。两人隔着五十丈的距离,同时张弓搭箭。
丁承用的是便于骑射的角弓,弓长两尺,制作精良。相形之下,对手的弓就粗糙了许多。木制的弓身长三尺有余,粗长的箭矢还是石制的箭头。
这样的距离不可能平射,两人都是望空斜射。一箭射出,两人同时催马上前。丁承那一箭不出所料落了空,而对手的一箭却紧擦着他的马头射进泥土。丁承惊出一身冷汗,立即拉弓射出第二箭。他的角弓窄小,虽然不能及远,但在射速上占了优势。对手发两箭的时间,足够他开弓三次。然而弓弦刚一弹出,一阵尖利的凉意便透胸而过。
谁也不会想到,那名射雕儿的动作会那么快。丁承的座骑刚奔出一步,那枚石制的箭头就射透了他的皮甲。马上的都护府军士溅血倒地,手里还紧紧握着他的角弓。
别矢里面无表情地俯身拔出自己的箭矢,驰归本阵,迎来族人一片欢呼。
马勇目眦欲裂,跃马冲上前去,吼道:“谁来与我比刀!”
“赤马翰!”
拔海刚唤出这个名字,一只手按住他。
“我来。”
马勇提着沉甸甸的长刀,热血像火一样燃烧。他是一名勇士,却不是一名好的统帅。他相信,凭自己的勇力能击溃所有的敌人,却没有想到,自己的鲁莽会带来什么样的灾难后果。
对面响起潮水般的呼声,“铁由!铁由!”
马勇狠狠呸了一声,盯住敌军出来的骑手。
马勇怀疑自己是不是看错了。那匹驰出的枣红马上,居然坐着一个矮小的家伙。除了头上那顶巨大的铁制头盔还像点样子,他简直就是一只骑在马背上的跳蚤。
马勇怒吼一声,长刀挥出。他这一刀,曾将金微山下的石柱拦腰砍断,就算那小子浑身都是铁打的,马勇也有把握把他一刀劈成两半。
两马相错,戴着铁头盔的小子举起长矛,朝上推去。那长矛黑黝黝不似木制,不过马勇此时居高临下,再加上座骑奔驰的冲势,想挡住他这一刀,无异于痴人说梦。
场中发出一声雷霆般的震响,正憋足力气的马勇胸口猛然一震,一口气顿时逆行回去。他那柄无坚不摧的长刀仿佛砍在一座山上,没有砍下分毫。他拼命握紧刀柄,却发觉手掌剧痛。接着他赖以成名的长刀便飞了起来。
后面的都护府军士看得清清楚楚。那一刀劈下,正砍在长矛正中。那个矮小的骑手横矛一托,就像磐石架住长刀。以悍勇闻名的马勇口喷鲜血,双手虎口都被震裂。戴着铁盔的骑手浑若无事,抬手挑飞了马勇手中的长刀,接着一矛刺进将军左胸,将他刺下马来。
那些都护府军士并不知道,他们面对的是铁由。流着古老英雄鲜血的铁由。
“祖先的血在你身上!”草原雄鹰铁什干说:“拿上你的刀!跨上你的战马!像苍狼一样追杀你的敌人!”
只有八岁的铁由就这样持刀跨马,开始了他一生的征战。三年来,无数次血腥的搏杀,为这个只有十一岁的男孩在部族中树立下不败的威名。
无论是罕多尔、拔海还是赤马翰,都对这位古老英雄的子孙尊崇万分。在他们心目中,铁由从来不会失败。
“铁由!英雄!英雄!铁由!”
嘶喊声中,战马潮水般卷过青色的草原。那两千丹华军还未接触到敌军便已经崩溃。丧失了斗志的军士们四处逃散,又被狼群般的敌人追上逐一杀死。
鲜血染红了青草,来自丹华的战士被马蹄践踏着,匍匐在泥土中,断肢和鲜血零乱狼藉。夕阳缓缓西坠,战场上矢刃交锋的锐响和濒死的惨叫交织在一起,血色的残阳映在折断的箭支和长矛上,这片肥美的草原犹如噩梦中的修罗场。
08





![Bizarre Life Vol.2 美囚隷嬢 憂花かすみ [大洋図書]](https://bdsmwild.com/wp-content/uploads/2023/04/00300-bizarrelife-bdsmwild-212-大洋図書Bizarre-Life-Vol.2-美囚隷嬢-憂花かすみ.webp)